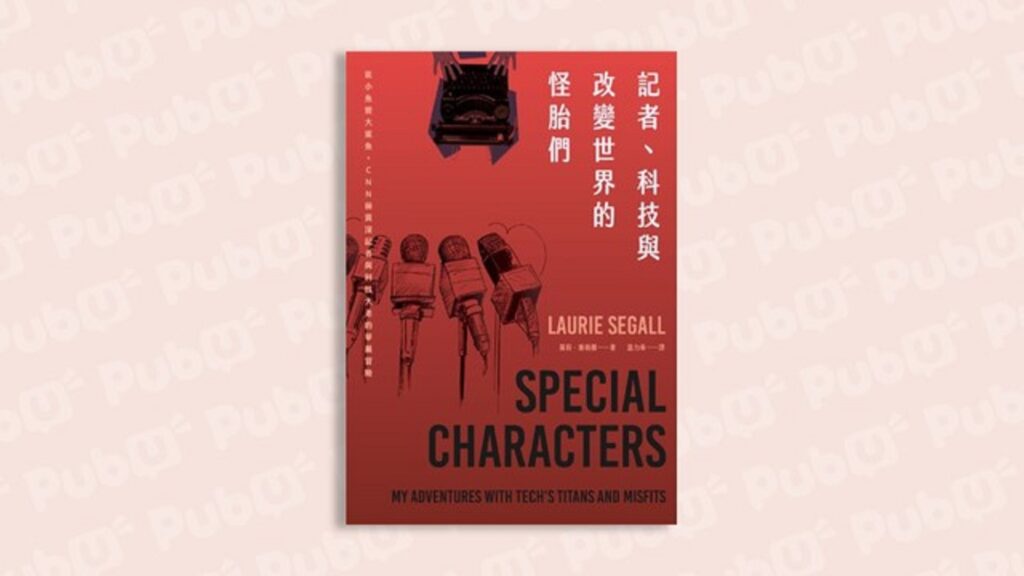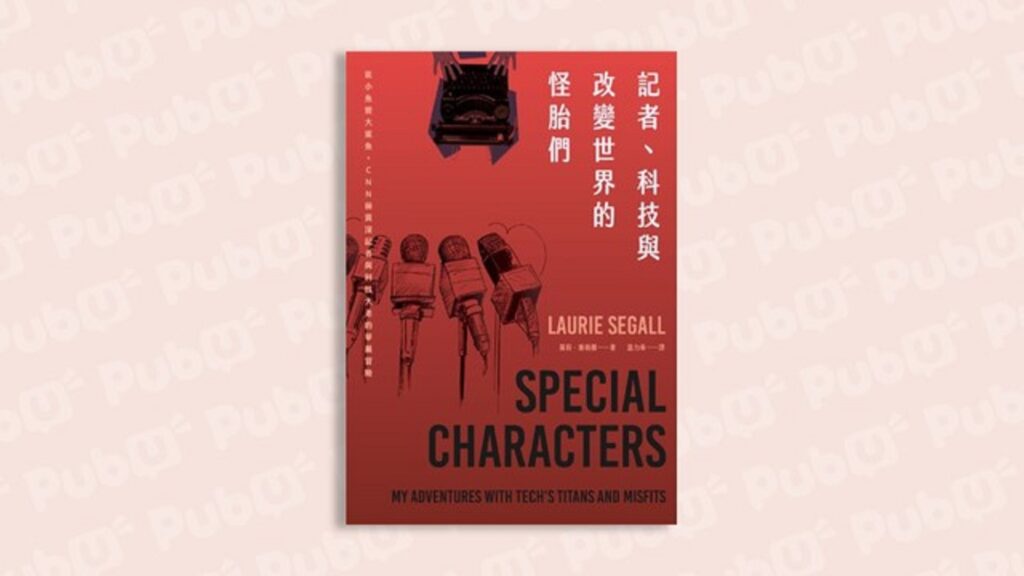二〇一〇年,一場科技運動正式發酵中。拜蘋果App Store大獲成功所賜,一個和斷垣殘壁的華爾街無關的新階級崛起了,他們是一群敢做敢為、跳脫框架的樂觀創業家。深夜和這些成長中的科技圈老班底聚會,是我的生活目標,我也開始思考該怎麼把這些非正式會面時的交流對話,轉化成不只是滿足好奇心的東西而已。我弟弟是個很有創意的傢伙,他對尖端先進的東西慧眼獨具,聽他說科技就是未來這句話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想對方向了。我在桑多西提咖啡館,向丹尼爾和黛比他們練習簡報我的構想,私下策劃如何製作科技新聞。
「你們覺得我有空的時候去採訪科技新創家如何?」
「你下午四點就下班了,一定有空的,」丹尼爾附議。
「我來拍攝,你來製作,」黛比邊說邊喝了一口馬爾貝克。「這樣一來上頭的人不必多做什麼事,自然就會點頭了。」
「史丹一定不會讓我做,他還是叫我麥金斯。」我忍不住抱怨我在《商業更新》的老闆。
「不如去問問迦勒?說不定他會讓你兼著製作新聞影片。」
迦勒是CNNMoney的主管,他的權力比史丹大,要是我這場在公司的棋局下得好,說不定有機會朝夢想成真邁出第一步,並且在新聞編輯部往上爬。我或許是個受訓不到兩年的製作助理,但我內心愈來愈清晰,眼下《商業更新》這個職位,只是一個等著被我真正想要的工作取代的位置而已。
隔天,我一邊奮力抵抗宿醉,一邊帶著滿滿自我懷疑的心情,朝著迦勒的辦公室走去,準備向他簡報我的構想。
先讓我採訪一位新創家就好,如果你不喜歡我們製作的影片,我就不再來打擾,我在心裡這樣複述,然後經過吱吱喳喳的新聞編輯部走道,來到迦勒的辦公室門前。
迦勒是一位十分幽默的年輕主管,有一種很酷的猶太教拉比的氣息,我在陳述想法時,他仔細聆聽:我會去採訪科技人士,給你有趣的報導,黛比負責拍攝,所以我們也不需要什麼資源,你不必多費心,只要答應我們就好。「剛開始我們先製作一個,如果你不喜歡,我們就當作沒這回事」我發表完最後的結論,雙手不知該放哪裡才好。
他猶豫地望著我,好像我是一隻會說話的松鼠。我把頭髮弄得直直順順的,拿出我最專業的穿著,也就是黑色合身外套搭裙子,期待這身打扮可以發出「力量套裝」的信號,然而我等待他回應的同時,卻覺得這身穿搭似乎暗示著「我正在參加自己的葬禮」,希望從我心裡一點一點地流失。
不過他接著露出笑容對我說道:「沒問題,塞格爾,你就試試看吧!」
「他要讓我們用公務車?」隔天黛比問道,雙眼睜得老大。或許是突如其來的好運,也或許是判斷力明顯失誤,總之迦勒同意讓我和黛比借用CNN的公務車。公務車通常都保留給專業攝影記者和知道該怎麼駕駛這種車的人。
「老實說,我也不敢相信。可是話說回來,我沒辦法在紐約開車。」
我上一次開車是五年多前在喬治亞桑迪斯普林(Sandy Springs)的郊區,現在駕照已經快過期了,想到要在紐約的車陣中鑽來鑽去,四周都是闖黃燈的瘋子,他們對單車騎士狂按喇叭,還會朝窗外咒罵大吼,就叫人心驚膽戰。
「我來試試看,」黛比說,聽起來不太可靠。
我和推特的三位共同創辦人之一畢茲・史東(Biz Stone)約好了採訪的時間。雖然這個現今已然是主流的媒體在當時尚未流行,不過公司正逐漸成為矽谷最炙手可熱的社群網絡。
我對黛比說:「他以為我是製作人,你覺得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我和畢茲來往了幾封電子郵件,在信裡我自稱「CNN的羅莉」。我並沒有「說謊」,但確實用「模糊地帶」避免揭露製作助理這個低階的身分。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黛比笑著抓起車鑰匙說:「演久就成真了!」
黛比駕著公務車出發往東村,我們把車窗搖下,廣播的聲音轟轟作響,我穿著Converse球鞋的雙腳放在副駕駛座前的置物箱面板上,我們選了聖馬可和A大道交叉口那邊的一張紅色長椅作為採訪畢茲的地點。當時,我已經搬到離原來住處再過去兩個街區的十一街,那是我的第一間獨立公寓,不過我覺得能在之前的街區拍攝訪問過程當作紀念是一件很棒的事。舊街區的視覺畫面很搭,又有鬧區的氣氛,要是讓科技咖坐在CNN攝影棚明亮的燈光下,實在太不妙了。不只是畢茲,就我聊過的科技人士,他們大部分都沒辦法適應政商名流和主播都很習慣的攝影棚燈光。這些科技人沒有伶牙利齒的口才,他們頭腦好,說起話來往往語句很長,未經過修飾。這場科技革新運動自由奔放,我們的採訪應該反映這種精神,攝影棚的環境太讓人窒息了。
我先在當地一家義大利餐廳和畢茲碰面,以便在訪問前先和他小聊一下。基本上,所謂聊一下就是我先自我解嘲一番,讓他敞開心扉多說一點,也讓黛比有時間把攝影器材就定位。
「嘿!」畢茲輕鬆地和我打招呼。他很年輕,看起來不是拘謹的人,身邊也沒有公關陪同。若要說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滿像會在飛機上先開口跟別人聊天的那種陌生人。
過了十分鐘,我收到黛比的訊息:可以開拍了。
「走吧!」我對畢茲說道,然後我們兩個走過一個街區到紅色長椅那裡。
我和畢茲坐在黛比的攝影鏡頭前,畢茲說了一個抽大麻的笑話,又講到他那位嬉皮太太讓野生動物在家裡隨便亂走的事。我拿出我希望是最專業的笑容聽他說話,一邊想像在西部某處有臭鼬和烏龜在充滿大麻的家中四處遊蕩的情景。我和畢茲坐在長椅上,對著一輛駛過的觀光巴士揮揮手,巴士上的乘客望著我們,一定在想這個身穿黑色上衣和牛仔褲,戴著金屬框眼鏡的男人是誰;沒有人知道這位先生以後會成為身價數十億美元的人。
「準備拍嘍!」黛比喊完便按下錄影鍵,毫無疑問,鼓勵我表現的比我感覺的還放鬆。
「推特(Twitter)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我問畢茲,同時也意識到黛比的鏡頭正對準我,我為自己能坐在鏡頭的這一邊感到幸運。製作助理出現在鏡頭上,這在CNN來講是前所未聞的事。一般而言,必須先在地方的新聞市場報導數年之後,才進得了CNN這種全國型新聞媒體的大門,得到在電視上露面的機會。我不曾在地方新聞媒體闖蕩過,以前也都不曾想過上鏡頭這種事。這些情況,畢茲全然不知。
我笑著說一些自認應該是萬無一失的話,但對於自己的聲音、雙手的動作還有該把手擺哪裡卻在意到令我痛苦。我知道我已經成功耍過體制,但資歷深淺恐怕不是可以造假的事。
「我們稍微討論了一下命名的事,」畢茲答道。「像『吉特』(Jitter)這個名字就出現過。」他笑著說,順便調整一下眼鏡。
「這樣的話,說不定我們原本應該說『發吉特』(jeeting),而不是『發推特』(tweeting)嘍?」我用了一點小小的幽默,然後再轉到更切題的內容。「你是個有豐富創意的人,你是如何衡量某個點子有多大潛力?」我繼續問道。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個點子有沒有讓你產生共鳴?這是不是你真心想做的東西,就算別人說這很蠢又沒有用處?」他回答。
這樣的觀點我以前聽過,我認識的很多創業家都有同樣的想法。這些試圖顛覆產業的創業家,總是會聽到業界質疑的聲音,比方說老經驗的員工或是墨守成規的人,根本搞不懂這些創業家想做什麼。這些外在的噪音說他們的構想一無是處,說他們不可能成功,還說世界有它應該有的樣子,我們應該用固定的行事之道,因為一向就是這樣行事的。這種觀念也是理所當然,畢竟大多數人不喜歡改變;改變不是常規。然而,創業家不理會這些噪音。
話說回來,常規對我而言反而陌生。我經歷過父母不願意坐下來商量,反而對簿公堂的情景;在我還搞不定青春期時就必須讓自己當個大人;我唯一的弟弟在我高中時去念寄宿學校,導致我們姊弟倆三年來幾乎都分隔兩地。
我不知道什麼是正常生活,不過我知道我恨透了「常規」。「常規」就是其他女人在校車站牌無視我母親,因為她們認為離過婚的女人是烙上標籤的壞女人。「常規」就是在沃什特瑙大道姊妹會會所的紅色大廳,和其他姊妹狂喝啤酒、聊著刻薄的流言蜚語。「常規」既苦澀又乏味,但是科技和創造科技的人卻是完全與「常規」相反的人事物,我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
採訪結束時,畢茲低頭看著我們坐著的長椅,有人在紅漆木頭上塗鴉,是一些名字和愛的宣言。
「我要不要也留下我的名字?」他開玩笑道,然後拿出一枝筆,把自己的名字塗寫在長椅上,在這個由他領路的數位世界,留下了代表他本人的象徵。
▍ 本文節錄自《記者、科技與改變世界的怪胎們》,羅莉.塞格爾著,天下雜誌出版。由Pubu電子書城授權轉載。